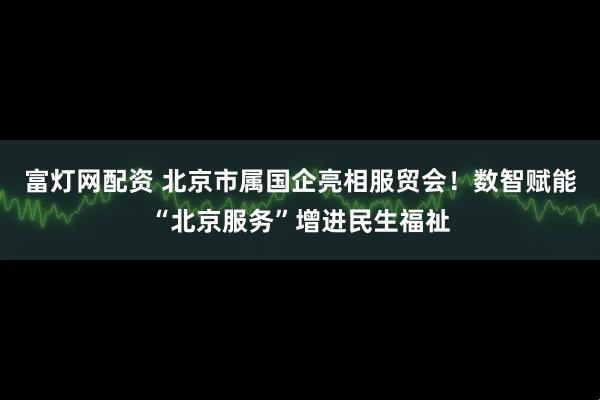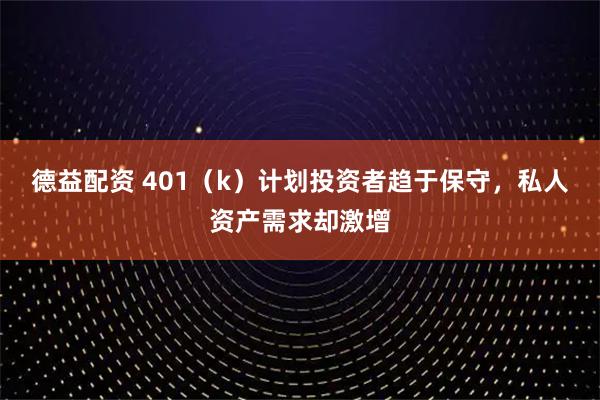他在哈尔滨的雪地里,站在一群青年中间,话不多,只是不时把帽檐扶正,看向台上冰雪节的火炬。2023年、2024年、2025年,他接连三度、四度以“带学生看世界”的姿态踏上大陆城市:南京、武汉、长沙,接着广东、陕西、北京,再到哈尔滨与成都,随后又计划福建、甘肃与更多华北华南的站点。与他昔日“得票七百六十五万”的掌声相比,这些行程显得温吞,却自有一种把热闹熬成清汤的坚执。他强调青年交流,认为胜过武器的叫嚣;他在孙中山纪念馆谈两岸和平,在湖南祭祖时听到“欢迎回家”牛盈宝,眼眶一热。那一幕,像一条细线,把他从政坛中心牵回个人身世的源头。
往来与求和:卸任后的路
卸任之后,他没有隐居。2023年3月27日,他首度赴大陆,带着三十多名台湾学生走南京、武汉、长沙。在南京的孙中山纪念馆,他把“交流减少误会”的逻辑讲得平平直直;在湖南祭祖,乡音与宗族的称呼让他说不出话。那一趟,他把抗战遗迹作为课堂,把“青年多走动比武器更强”作为课堂。
这之后的步伐更密。2024年4月1日至11日,二访大陆,路线从广东至陕西再入北京。深圳见到了国台办主任宋涛;在西安城墙上,他带学生读城砖;进北京故宫,让这些青年在午门下按图索骥。清明那天,他参加公祭轩辕黄帝典礼,仪式里的肃穆,为这趟行程添了古典意味。到了当年年底,12月18日至26日,他第三次踏上哈尔滨与成都:前者是海峡两岸青年冰雪节,后者是三星堆博物馆与德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;其间,与四川省委书记王晓晖、省长施小琳会面,话题仍未离开“青年互动、民间交流”。
展开剩余86%2025年的安排干脆更像一张密密的课表。6月11日,国台办宣布他将于6月14日至27日率台湾青年赴福建、甘肃,出席第十七届海峡论坛、公祭伏羲大典、两岸共同市场合作论坛。海峡论坛下设青年、基层、文化、经济四大板块,共56场活动,他表态全程参与。6月14日从桃园机场出发,他对媒体说,希望两岸青年能够互学,这对和平有帮助。到了7月4日,他又预告暑假要带学生去北京、广东、广西、重庆、天津、上海。名义上,这些活动由马英九基金会运作,但其内里,是他把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的节奏迁回民间的尝试。
小科普:对两岸而言,青年交流并非新鲜词。不同的是,昔日官办会谈居多,卸任后由前任领导人亲自带队,既避开政治谈判,又保持象征意义。参加如“公祭伏羲大典”“公祭轩辕黄帝”等古礼,强调共同文化谱系;海峡论坛的多板块设计,则对应社会层面“多点接触”的策略。
家门之外的标签:两个女儿的反向选择
对旁人而言,他是领导人;对两个女儿而言,他是让她们必须绕道而行的父亲。大女儿马唯中,1980年11月生于美国,从小在台北念书,成绩耀眼,1998年高中毕业拿下台北市长奖,当时按规定本可直入台大动物系。但媒体质疑“父荫”,她不愿背口水,转身飞赴美国求学。她在哈佛完成本科,又到纽约大学读博物馆学硕士,工作上从艺术家蔡国强工作室的助理干起,一步一步到项目经理;2017年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拿到艺术史博士。婚姻上,她在2012年与哈佛同学蔡沛然结婚,婚后先居香港,后举家搬往纽约;2019年怀孕时回台小住,产下儿子,如今一家在纽约安家。2022年,她入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,任亚洲艺术副策展人,工作与生活的重心在美国与香港,很少回台。
小女儿马元中,1985年11月出生,性格更活络一些,同样在台北完成小学到高中,也曾获台北市长奖,并有机会直升台大历史系。她看见姐姐的境遇后,做出类似决定:2002年高中毕业便赴美就读布朗大学艺术系,毕业后留在纽约做策展人,偶尔与姐姐合作项目。两姐妹默契地“避开光环”,父亲坦承女儿远走是为避麻烦,他觉着亏欠。2005年祖父马鹤凌去世,她们回台参加葬礼,那或许是这个家最后一次整整齐齐。2009年春节,她们留在美国过年未回台;此后几年,因母亲病况或重大场合才飞回。姐妹之间的联系倒是紧密,只是“马英九女儿”的标签,她们更愿在海岸的另一端消化。
小科普:台北市长奖是对学业与公共参与成绩突出的高中毕业生的表彰;“保送台大”在当时是一种对优异生的制度性通道,但在名人子女身上,往往被舆论解读为裙带,因而在社会层面带来反向激励。
家庭根与宗教:湘潭家族与天主教家风牛盈宝
这段关于“回家”的情绪,源头要回到1950年。他出生在香港,祖籍湖南湘潭的客家人;两岁时随父母迁往台湾,定居台北。父亲马鹤凌是国民党中层干部,母亲秦厚秀在家带孩子。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,上有三姐,下有一妹,自小被众星拱月。家里信天主教,他八岁时在香港受洗,回到台湾后依旧每周去教堂。这种宗教生活的规律性,成了后来他身上那种“按部就班、耐心等待”的气质底色。
学成与起步:从海军陆战队到哈佛博士
如果说家世是缓慢的回响,那么教育则是他上升的直线。幼时读静心幼儿园、台北师范附小、再到大安中学、建国中学,每一步都踩在台北教育系统的尖端。17岁加入国民党,既是青年投身党国体制的寻常,也是他后来政治身份的前奏。1972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,曾在美国转了一圈,在旧金山寄宿家庭住了三周,初见制度与生活的差异。之后服两年海军陆战队役,退伍后拿国民党奖学金赴纽约大学完成硕士学位,1976年毕业;继而进入哈佛大学,1981年获博士,论文聚焦东海油气纠纷,并出版成书。这类选题既是国际法的专业关怀,也回应东亚地缘政治的现实。
在美国求学时,他结识了周美青,两人于1977年结婚。1980年11月长女马唯中出生,1985年11月次女马元中随之而来。1981年全家回台湾,蒋经国看重其“家世干净”,延揽为英文秘书。对当时的体制而言,英文秘书并非单纯文书,更多是传达与窗口,既能近距离观察权力中枢,也能以“技术官僚”的方式进入决策外圈。1982年他正式到任,自此“秘书型官员”的路径渐行渐稳。
小科普:当时的“党国体制”下,国民党与政府高度交织,技术型人才往往从秘书、研考、法务等部门起家;海军陆战队服役两年则是彼时知识青年普遍的国防义务经历,常被作为锻炼心志的资历。
升沉与风声:政坛中的快与慢
从英文秘书起步,他很快完成了从“辅佐者”到“操盘者”的跨越。1984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;1988年升任行政院研考会主委,并兼任大陆工作会报执行秘书,这个岗位把他与两岸事务的线索缠在一起。1993年,他接下法务部长的职务,主打查贿与童妓案,强调“依法治国”的姿态,在任内犯罪率下降不少。法务官出身的“硬度”难免得罪人,1996年他转任行政院政务委员。
从中央转向地方,1998年他以反转胜的气势赢得台北市长,击败陈水扁;四年后在2002年高票连任,得票率达64%。地方治理的成绩把他推上党魁之位,2005年出任国民党主席。然而2007年特别费案遭起诉,他请辞主席,但并未击破其民意基础。2008年,他以765万票的成绩击败谢长廷,当选领导人;这既是个人高峰,也是国民党再度执政的标志。2009年他重掌国民党,2012年成功连任领导人;至2016年卸任,整体路途颇为顺畅,却“顺”中带“争”,既有革新的主张,也受制度与社会裂缝牵扯。
小科普:“特别费案”所涉,是地方首长与高阶官员的行政特别费使用规范,在彼时法律与实务之间存在模糊空间,引发司法与政治的交错争议。至于台北市长在台湾政治中的位置,既是治理能力的展示台,也是领导人之路的“必经关”,不单看市政,更看动员、形象与危机处理。
空巢与一只狗:政治家的日常缝隙
政治与家庭的钟摆,有时并不同步。1999年他担任台北市长时,市府推动流浪狗领养,他带头领养一只混种犬,取名“马小九”。进门后不久,家里多了脚步声;周美青格外用心,把它视为孩子,固定喂食、定期带去兽医检查。这份日常的琐细,和外界对“明星政治家”的印象形成对照。两位女儿相继远行,家中渐渐清静,卸任前公务裹挟尚不明显,卸任后空落更显。2005年父亲马鹤凌离世,姐妹返台奔丧;2009年春节,姐妹在美国度过,未回台,这之后多半在母亲生病或重大场合才飞回。她们的人生选择与父亲的公职安排像两条延伸的轨道,偶有交汇,又各自延伸。
从台上到课堂:自我定位的转身
他后来常说,通过对话消解误解。与昔日站在讲台上、镜头前不同,现下的他更像扛着背包的领队。深圳见宋涛,是礼节性的沟通;西安城墙、北京故宫,是历史的缝合线;哈尔滨的冰雪节与成都的三星堆,是文化的“轻而盈实”。走到德阳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,又把科技与安全议题轻轻点到;见四川省委书记王晓晖、省长施小琳,则是人情与制度的接口。2025年6月在福建与甘肃,参与海峡论坛、公祭伏羲与两岸共同市场合作论坛,恰好把“青年—文化—经济”的三角搭起来。离开权力的庇荫,他试图用一个前任的分量,为下一代打开几扇窗。
小科普:两岸共同市场合作论坛的议程往往聚焦产业互补、标准对接与企业交流,不等于签协定,却能铺设合作语境。类似的论坛在有效期内能形成“次结构网络”,为正式谈判蓄温。
起点与背影:制度中的个人
回望他的起点,会发现许多线头从少年就缠上。17岁入党,意味着早早进入体制的路径依赖;台大法律系奠定专业底盘;在旧金山寄宿三周让他看到美国的社区自治与生活节律;海军陆战队两年的兵役,在许多台湾男性中被视作“成人礼”。纽约大学的硕士、哈佛的博士,让他同时具备“国内训练的严谨”和“国际法视野的打开”。1981年返回台湾,蒋经国选他做英文秘书,既是家世清白、背景单纯的考量,也是对新生代技术官僚的布局。
而他与周美青的结合,在当时是“学术共同体”的自然延伸:她对家、对狗、对孩子的照料,让这位政治家有了一处现实的锚。他的两个女儿,一个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亚洲艺术为职场,一个在纽约的策展圈打拼,偶尔合作策展项目。她们选择的城市与职业,离政治逼仄的地带恰好最远。
人物的命运并不全依赖外在事件。有人爱提他的“争议”,但当他在南京讲和平、在湖南祭祖、在北京故宫带队、在哈尔滨踩雪、在成都看三星堆时,争议变成背景噪音。他身体尚好,偶尔露面讲话,语气比过去慢了半拍。风光与落寞他都经历过,如今更在意的是可以把话讲给谁听,如何让年轻人自己去看、去判断。
余音:标签、选择与“心安”
他的人生像是两条长线的缠绕。一条是制度给的:党国机制、秘书岗位、法务改革、市长连任、党魁与领导人的高位、再到卸任后的象征性访问。另一条是家庭给的:湘潭的客家根、天主教的节律、三个姐姐与一个妹妹的家常、两个女儿的离开与偶尔的归来,以及一只名叫“马小九”的狗。2012年的连任与2016年的卸任,是制度线的标点;2019年女儿回台待产、在纽约育儿,是家庭线的波纹。
他把这两条线在卸任后编织成第三条:教育与交流。把政治语言降温成课堂的语气,“青年走动,误会便少”,这话他一遍遍说。他知道,公共舞台的掌声早已淡了,留在他手里的,是时间与耐心。像他年轻时每周去教堂的习惯,像他在舆论汹涌时仍按制度路径回应特别费案,像他在台北推领养时自己先抱回一只流浪狗。这些看似零散的动作里,有一种想要“图个心安”的秩序感。他并不否认自己曾站在高处,但当他领着学生从厦门的会场走向天水的伏羲庙,从天津的码头再到上海的展馆牛盈宝,那些高处的记忆已化作一条条路径上的里程碑,提醒他何以而来,又将去向何处。
发布于:天津市创通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